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 检察日报社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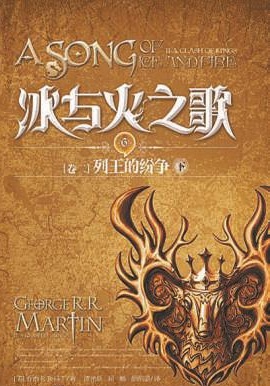
《冰与火之歌》:凛冬将至,我们能否以死赴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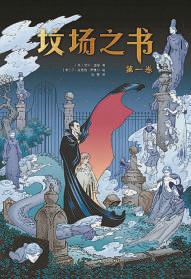
《坟场之书》:以爱滋养的孩子,在任何地方都能够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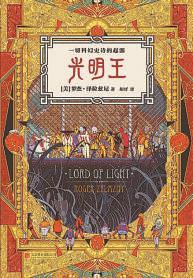
《光明王》:技术垄断造就出宗教伪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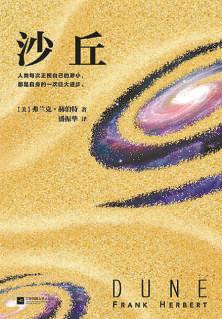
《沙丘》: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
西方幻想文学中的法律与宗教也多有现实影射。科技与宗教都在探寻存在的本源,法律与神性均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读懂西方幻想文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懂这个曾给中国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西方。
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面对20世纪70年代欧美等国法律与宗教脱节、法律逐渐失去其神圣性的现象,哈罗德·伯尔曼提出:“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对英美的法律制度与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的联系作了鞭辟入里的阐述。此种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形,在西方幻想文学中也多有呈现,细查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法律与宗教的联系。
1.
有异于世俗政权中法律与宗教的泾渭分明,在欧洲历史上,宗教不仅深深影响法律原则、规则、程序等的形成和实施,而且曾经就是法律本身,甚至成为超越法律的社会规范。宗教教义这种基于终极关怀形成的超验直觉和奉献,轻易将世俗法规范实践中的权威树立和普遍遵从之困境破除,相对于道德、礼仪、习俗、皇权指令等,具有明显的优先拘束力。西方幻想文学中不乏描述法律与宗教的交融状况的内容。
一是明确提出教义即法律。在科幻巨著《沙丘》系列小说中,人类足迹已经遍布银河系,组成一个广袤的帝国,但政权体制却与欧洲中世纪皇权、教权相结合形态极为相似:皇权之下的贵族阶层等级森严,类似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组织对政权牵制能力强大。男主角在如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故事发展过程中,为了取回原属于其父亲的公爵权力,既要在皇权、教权和自身婚姻、继承权等之间小心斡旋,又要时刻警惕通过特殊预知能力预见到的极端宗教战争风险。宗教及其严格的教规教义,为整个故事的走向抹上了一层厚重而神秘的色彩。
二是彰显教义的广泛约束力。在获得雨果奖的奇幻小说《坟场之书》中,公共墓地成为幼年时期主角的庇护所,可即使在这个逃离了一般世俗法则禁锢的魂灵之地,往生者们也要受到宗教的规制。公共墓地是世人赐福给教堂并由其辖制的圣洁领域,但墓地仍有边界和禁忌,在墓地旁边,专门留出了一块不圣洁的土地——制陶人之地,用以埋葬罪犯、自杀或者不信仰基督教的人。
三是审判制度契合宗教而产生。在奇幻名著《冰与火之歌》中,维斯特洛大陆上流传的宗教包括七位一体的七神教、森林之子的旧神教、崇拜光明的拉赫洛教、源自海洋的淹神教、面目多变的千面之神教等,其中七神为大陆上七国遵从的主要宗教,影响了各国的婚姻、继承、财产、政权组织,甚至诉讼程序。例如,裁判罪行的七子审判制度,即按照七神信仰,由诉讼双方各找七人参加比武,以体现对七位神祇的崇敬,诸神也将据此作出有罪或无罪认定:若一个人找不到六个相信自己、愿为自己而战的人,这个人显然有罪;若双方均七人成行,骑上战马、装备甲胄、携带武器不论生死比武之后,被裁判之人一方取得胜利,即表示神裁定其无罪,否则,其将遭受极刑。
2.
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旨在慰藉心灵提供寄托的宗教,其产生要远早于世俗意义上的法律,甚至可以说,宗教礼仪、教义、禁忌等曾一度发挥着当代法律的作用,教规不仅仅是约束宗教内部人员和教众的,更是一种发挥核心控制功能的社会规范体系,宗教经典即是法律条文。可随着世俗政权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具备特殊内容和专项技术的世俗法逐渐与教会法相分离,王权开始与神权对抗并相互掣肘,这种分权制衡的状况,成为当代欧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治学说之滥觞。西方幻想文学中描述王权与神权制衡发展的不在少数。
一是借鉴欧洲发展史。在阿西莫夫所著的《基地》系列小说中,预见到庞大的银河帝国人类文明即将崩溃,陷入长达三万年的,充满无知、野蛮和战争的黑暗时期的心理史学家,以编撰“银河百科全书”为由,将部分优秀科学家带至银河系边缘一颗荒蛮、贫瘠的小行星,试图建立一个“基地”,以其为基础,将原本需要三万年的人类文明重启时间缩短至一千年。作者顺次安排了政治制衡、宗教联合、商业贸易几个阶段,此过程与欧洲历经蛮族入侵古罗马帝国后的文明凋落,教权强大的中世纪,而至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后对外贸易扩张的崛起路线何其相似,宗教对整个欧洲近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是凸显宗教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在罗伯特·西尔弗伯格根据同名短篇演绎成的长篇小说《日暮》中,作者虚构了一颗拥有六个太阳的行星,白昼成为常态,每隔两千多年才会迎来一次黑夜,星球上的人们不知黑暗为何物。在黑暗陡然降临的那天,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末世恐慌,为平复这一混乱景象,科学家与坚称神力彰显的教会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最终,宗教势力凭借大众对黑暗的恐惧心理掌控了世界,宗教禁令成为法律,科技进步受到重挫。小说对科学思想和开明文化的普及提出了警示,而对宗教的保守和僵化保持一定警惕。
三是利用宗教相对于世俗世界的独立性传承文明的种子。在经典科幻史诗《莱伯维茨的赞歌》中,面对人类科技文明宿命般的一次次经历思想解放、高速发展、到达顶峰、战争毁灭的周期轮回,部分精英有意识地通过教会的修道院将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抄写和保存下来,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以修道院的独立于世悄然承担起救世的重任。在文明短暂地坠入黑暗和蒙昧时,主动向外界散播科技的火种;在文明狂飙突进自我毁灭时,持续抄录并通过各种方式与时俱进地为后世保留文明重新崛起的微光。公元3781年,经过一代代教士的努力和传承,修道院在地球行将因核战而彻底毁灭之前,将辑录的知识和部分教士送往了太空,开启了又一个文明复兴的循环。
3.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对所有社会活动都有相当的控制力,各国都处于神权统治之下,政教合一成为常态,神权往往高于王权,教会法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最高等级的法律。随着时代的发展,旧的教规教义因刻板僵化而愈发成为束缚文明进步的枷锁,不同宗教或宗教派别的兴起与运动,逐步从思想上解放了人们,“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法的发展演变、世俗法与教会法的分离、世俗法体系的逐步完善等,成为推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科技等创新和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西方幻想文学光怪陆离的外衣下,也有的将宗教演进的影响渗透其中,呈现出别样的韵味。
一是将文明进步与宗教演化巧妙结合。美国科幻作家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系列小说的故事背景为,人工智能成为一种新的能够交互作用、新陈代谢、不断进化的“生命体”。当人工智能将创造其诞生的人类视为存在竞争关系的种群之后,为其自身长远发展,故意制造了失败的黑洞试验,使得地球被微型黑洞逐渐吞噬,试图削减人类数量、限制人类文明。尽管人类并未受此影响,反而实现了星际拓展和殖民,但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进化之争仅仅只是刚刚拉开序幕。
人工智能预测和人类宗教预言中的未来决战均与一颗偏远星系的行星“海伯利安”相关,一支由7名朝圣者组成的探险队向海伯利安进发,他们出身不同、职业各异,包括天主教神父、圣徒、学者、侦探等。途中,各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从不同层面呈现了人类文明的前景和危机、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交缠和争斗、寿命接近永生之后的欣喜和苦恼、不同种族之间爱情维系的艰难和希望等终极意义上的拷问。朝圣之旅的终点,众人到了海伯利安,一切谜题似乎即将解开,却仅仅是延续好几百年的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进化争斗的序幕。
二是以不同宗教间的对抗启发民智、推进改革。“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皆与魔法无异。”这是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名言。罗杰·泽拉兹尼的经典科幻小说《光明王》就描绘了凭借高等科技伪装神祇的场景。开创世界的最早人类“原祖”,通过将意识传输入年轻躯体而获得永生,凭借超越世代的技术成为“神”。这些神在古老地球印度教的外衣下,将自己伪装成创造之神梵天、毁灭之神湿婆、保护之神毗湿奴等神祇,科技成为“神性”“法力”,而凡人必须向神效忠、奉献,若有反抗,将遭受死亡的命运。这样的法律制度当然遭到了部分怀有良知的“原祖”反对,他们试图像普罗米修斯一般为凡人盗取文明火种。经过阴谋与爱情、战争与妥协、背叛与救赎之后,新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建立了起来。
经过多年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幻想文学已经俨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深刻影响影视创作、科普宣教、民众阅读等领域,同时,与之相对,西方幻想文学中的法律与宗教也多有现实影射。某种意义上,科技与宗教都在探寻存在的本源,法律与神性均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理解了西方世界的历史,才能真正读懂西方幻想文学,而科技预测或奇思妙想下的幻想文学世间生态,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懂这个曾给中国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西方。
京ICP备13018232号-3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30016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京B2-20203552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0425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0541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京)字第181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京零字第220018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702000076号
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642 3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