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 检察日报社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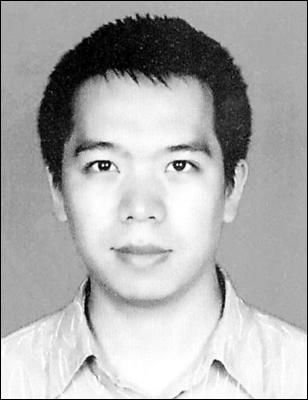
海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王琳
《检察日报》11月28日报道了上海市检察机关全面推广试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消息。这一制度此前已在6起案件中试行,污点被限制公开的6名涉案未成年人中,4人顺利就业,1人顺利复学,1人考上了大学。
“污点限制公开”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的《梅根法》。梅根是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女孩,1995年被一个曾两次入狱的儿童性骚扰者强奸致死,强奸犯与梅根住在同一条街上。为保护儿童权益,当时在位的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梅根法》,该法规定危险的性骚扰者或强奸犯出狱并迁入某社区时,当地官员应向该社区公开其犯罪资料,以便大家对他保持警惕。《梅根法》在美国引起了激烈争议,反对者认为,公布前科是对迁居人隐私权的侵犯;支持者则认为,如果这种公开隐私有利于保护更多人的利益,就构成侵犯隐私权的“合理抗辩”,因此并不违宪。现在美国已有49个州立法要求登记被定罪的儿童性骚扰者,其中30个州规定有性侵犯儿童前科的人在迁入某一社区时,当地官员应通知该社区。
很显然,在美国,保护隐私权包括有前科者的隐私权是一般原则,《梅根法》是基于公共利益考虑的一个例外。而上海推行的“刑事案件污点限制公开制度”,是以公开为一般原则,以“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轻微,限制公开污点”为其例外。《梅根法》旨在保护大多数人的权益,“刑事案件污点限制公开”旨在为少数未成年犯罪人的复学、就业“创造有利条件”。从立法的精神来看,法律虽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但也不能放弃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尊重多数,保护少数”一直是立法和司法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
理论容易解释,而实践中,多数人权益与少数人权利的调和却不是三言两语就可达成的。事实上,所谓“刑事案件污点限制公开”并非上海首创。早在几年前,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等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就在全国率先试行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这一制度一经实践便遭遇了法律与民意的双重困境。如同死刑在中国的存废问题一样,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专家与民众之间看法不同,尖锐对立。专家们从美国犯罪学上著名的“贴标签理论”出发,认为被贴上“犯罪人”标签的初犯者,由于这种标签即作为前科的犯罪记录的存在,将再次被推上犯罪道路。而民众则将“前科制度”视为国家和社会自我防卫的需要,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往往通过各种形式的犯罪予以释放,对于大多数善良的民众来说,来自犯罪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也令人感到忧心,并寄希望于国家对公共安全和秩序进行有效维护。生活在社区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与已被审判机关确认的“犯罪人”隔离开来,“前科”和“污点”正是实现这种区分的最简单的工具,而知悉一个人有无“前科”和“污点”,其前提便在于司法公开。
在“前科消灭”制度的试行难获好评之后,有专家称,目前在中国实施“前科消灭”的各方条件还不成熟,而“限制公开”是对犯罪记录有条件地、暂时不予公开,“这对失足少年顺利回归社会,防止他们再次犯罪十分有利”。然而,以此作为对未成年犯罪人“污点限制公开”的理由,仍然难以逃离法律与民意的双重考问。在法律上,不起诉决定书与判决一样,均应无一例外地予以公开,没有特例;而且,大多数人仍然倾向于认为,有前科者欲回归社会只有自我救赎,不能没有改过表现就向社会预支一份宽容,对于一个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明真心悔改的有前科者,社会并不会因他身上的“犯罪标签”而歧视他。
当然,一些特定行当绝对禁止有前科者进入。我国刑事立法就详细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即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应当如实报告自己受处罚情况。与“前科报告”制度相联系,《教师法》、《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均规定,有过犯罪前科的人不得担任教师、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在笔者看来,“限制公开”虽然能够保障“属于弱势群体的未成年犯罪人”工作和读书的机会,但这种“合法”的隐瞒犯罪记录的做法一旦铺开,对于绝对禁止有前科者进入的某些行当而言,意味着即刻失去了直接考察和了解即将成为员工的人员此方面基本情况的可能性,这种负面效应能被忽视吗?这是否会造成混乱?
京ICP备13018232号-3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30016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京B2-20203552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0425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0541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京)字第181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京零字第220018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702000076号
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642 3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