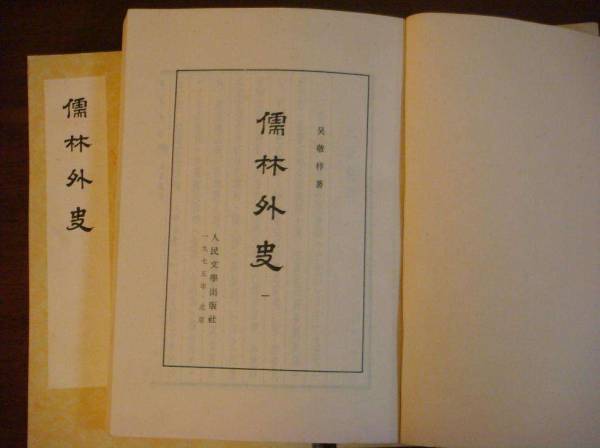
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写实辛辣的笔法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官场的黑暗给予了无情的揭露、批判,被誉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巅峰之作。该书除了巨大的文学价值之外,还真切保存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百态,特别是书中对司法案件的描写,将冰冷的法律条文还原为具体生动的人的意识与实践,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绝佳样本。
今天笔者结合《儒林外史》中的几则案例,谈一谈古代司法实践中的请托现象。
案件请托 所在多有
请托干预析产继承案件。第六回“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中,严致和之妾赵氏在正妻王氏病故前,由严致和主持、在亲族见证下被立为正室。后王氏、严致和相继病故。赵氏的大伯子严贡生主张赵氏存在妾身、无子、非家主等资格瑕疵,否认其掌管财产、立嗣的权利,意欲霸占赵氏的家产。双方协商未果而呈讼,知县一审以“律设大法,理顺人情”,判决支持赵氏(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知府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仰高要县查案),知县重审后做出同样的判决,知府则予以维持(如详缴)。严贡生不服,赴省会申请再审,遭到按察司的拒绝(细故赴府县控理)。严贡生又进京上访,同样吃了闭门羹。走笔至此,作者便翻过这一页,开始讲述其他人的各种荒诞故事,又是“范学道视学报师恩”,又是“王员外立朝敦友谊”,又是“王观察穷途逢世好”,拉拉杂杂,好不热闹,就是不提赵氏与严贡生一案。读者心想,这个案子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怕是已经办成铁案。哪知道一路行至第十八回“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突然峰回路转。借着胡三公子不经意的一句话,我们才知道严贡生“到处乱跑”之下,最终案子被再审改判为赵氏分得三成家产,严贡生的二儿子被立嗣并得到其余七成。请托之力,由此可见一斑。
请托免除债务责任。第九回“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中,盐店管事杨执中经营不善,致盐店亏本七百余两而无以赔偿,被店主控告后拘禁在监。两个娄姓公子哥路见不平,让管家递去一份禀帖,先说愿给杨执中作保,次则断言知县拘押违法(盐店的银子非赃非帑,何以便行监禁?),让知县看着办。这个请托,更准确地说,其实是用权势压人。要知道这两个请托者的令尊大人可是前内阁大学士,根本不是一个小小知县所能得罪的起的,他只好乖乖放人,自己还要想办法筹钱补上盐店的亏空。
请托影响婚姻案件。第四十回“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中,沈琼枝嫁与宋盐商,后者却只给了她妾的名分。沈父气愤不过,一纸诉状告到县衙。知县阅卷后的初步印象是“盐商豪横一至于此!”最后的判决则是“(沈琼枝)显系做妾可知。”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还在于宋家“打通了关节”。
请托了结人命官司。第四十四回“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中,在一起涉及人命的案件上,知府主动要求其友余有达充当司法掮客,安排余有达主持被告人与被害人家属“私了”,然后再向知府开展关说,最终实现“案结事了”,知府和余有达也各得银子百余两。
请托排除“高考移民”审查。第三十二回“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中,科考在即,张俊民的儿子是个“冒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移民”,本身没有应试资格,只因公子杜少卿给打了一声招呼,又出了一笔捐修学宫的赞助费,“高考移民”的资格障碍便不存在了。
请托解决“公务员编制”。第五十回“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万里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为了告别“喝风痾烟”的苦日子,便假扮“在京保举中书”,到处招摇撞骗。结果不慎卷入一件刑事案件中,后经友人凤鸣岐多方运作,居然弄假成真,变身为真的中书,并借此身份逃出了刑罚牢笼。
以上案例所揭示的司法请托现象之猖獗,令人不禁怀疑《大明律》(作者假托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到底对请托有没有规制?这些规定在现实中有没有得到执行?
惩治请托 有法可依
请托,指的是请托者以人情为据或以权势威胁,要求掌握公权力的受托者通过曲枉法律来实现请托者的不法利益。这种以言辞干预司法或行政活动的行为,也可称其为说情、嘱托、听请、说请、请谒、关说等等,不一而足。其词虽异,其义实一,以请托一词最为常见。
请托正是为着干扰公权力而产生的。陕西扶风曾出土过一件名为“琱生簋”的青铜器,其上铭文记载,公元前873年,触犯法律的被告人琱生通过向主审法官召伯虎请托而顺利逃脱了罪责。
古人云:“请托一事,伤人害物,长刁纵恶,莫此为甚。”请托不仅会严重腐蚀公权力,危害社会公正,快速消解政府公信力,更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源头。因此,我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对于请托之禁堪称严格、完备至极。
以明代为例,《大明律·刑律·杂犯》的“嘱托公事”条规定:
凡官吏诸色人等,曲法嘱托公事者,笞五十。但嘱即坐。当该官吏听从者,与同罪。不从者不坐。若事已施行者,杖一百。所枉罪重者,官吏以故出入人罪论。若为他人及亲属嘱托者,减官吏罪三等。自嘱托已事者,加本罪一等。若监临势要,为人嘱托者,杖一百。所枉重者,与官吏同罪。至死者,减一等。若受赃者,并计赃以枉法论。若官吏不避监临势要,嘱托公事实迹赴上司首告者,升一等。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条文对请托的基本类型、定罪标准、量刑幅度、举报奖励等事项都做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其一,本条特指纯粹的人情请托,当与伴有财物往还的贿赂罪相区别;其二,请托者不能免于处罚,如本身有公职,要加重处罚,概因其知法犯法之故;其三,请托系行为犯,受托者一旦口头应允所托之事便属既遂,若已施行则加重处罚;其四,分别就为他人亲属请托、为自己请托、以权势相压请托几种类型列明不同的处罚标准;其五,受托者举报有奖。清承明制,请托的法条一体沿袭下来。
不难想象,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已将请托视为影响司法官员正常办案的绝对障碍,惩处力度不可谓不大,规范程度不可谓不细,假如能得到有效认真执行,则请托之风必息,司法必归于清明。然而,事实上从《儒林外史》中的描述来看,惩治请托的法律并未得到有效贯彻,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律法俱备 缘何未行
明代大学士张居正有一句名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中国古代社会以人情礼义为构成基础,请托现象普遍存在,三个影响因素亦贯穿其中:其一,经济利益的诱惑——接受请托,就可以权力寻租;其二,客观环境的限制——不接受请托,无法在当时的官场上立足;其三,官员自身的修为——是否秉持不畏权势、不顾私情的理念。因此,对一般官员而言,如何既能做到清廉,不受请托的干扰,又能遂顺人情,协调情与法、情与偏的矛盾,始终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有一个解决方案颇具代表性,即“如法不违也,做人情不妨。如违法,虽权贵亦不可听也。”或者“若有至情相托,须委曲处之,但不可病民。”很明显,这种做法极容易混淆私情与公义,常常只管情感而不问曲直,只顾私谊而不计公利,然而它却是一种普遍心态。当大多数的官员在请托问题上保持拒大放小这一看似符合儒家中庸思想的态度时,本质上是当时整个官场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最终事实上搁置了请托之法。
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儒林外史》中,不仅没有哪个官员在受到请托时去积极举报,也未见到哪一个请托者因请托而受责罚,反而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通过请托来化解,请托者与受托者在主动与被动之间,心安理得、行事自如,请托之法竟好似不存在一般。唯一的亮点,也仅见于梨园出身的小吏鲍文卿在面对请托时,用“公门里好修行”来加以婉拒。饱读诗书的儒生们与目不识丁的戏子在请托问题上的表现相形比较,便高下立判,一种莫名的讽刺感也油然而生。《儒林外史》之所以伟大,正在于此。
即便在今天,请托现象仍不鲜见。
前车可鉴,殷鉴不远。正是鉴于个别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审判给司法公信力和社会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损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此后,中央深改组和中办、国办分别印发了相关规定,明确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了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架起过问案件的“高压线”,为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了制度保障。
有道是,人生多歧路,请托者勿玩火自焚;公门好修行,受托人当三思而为。《儒林外史》中的请托故事,至今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作者单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京ICP备13018232号-3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30016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京B2-20203552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0425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0541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京)字第181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京零字第220018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702000076号
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642 3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