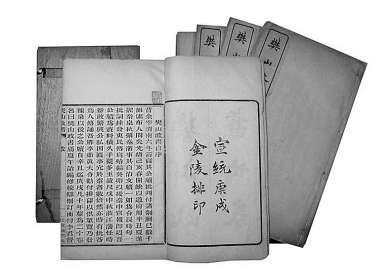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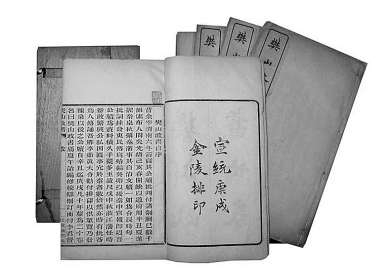
《樊山政书》影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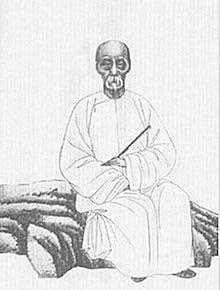
樊增祥画像
《樊山政书》,是樊增祥1901年至1910年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和江宁布政使时所写的公文合集,这些公文大多是关于民众上控以及下级案件汇报的批词与判词等司法文书。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逐渐解体、近代法制开始创设的阶段,《樊山政书》可以说是“旧式”司法技巧、理念的绝唱。对于“尚文”的国度来说,坚持原有的司法文风是一种惯性选择,传统司法公文自有其独特的个性与优势,但在法律转型时期的潜移默化中,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对于《樊山政书》中传统司法文体“变”与“不变”的考察,有助于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结教训、汲取精华,服务于当代司法文风的完善。
传统司法文体的特质
司法文风首先与司法人员的气质相一致,可用“伦理、词章”概括。伦理的根本是忠孝,这是本原;如果道德不行,便是文字再好,也不可称道。文字是道德的外化,法律文书作为一种文字形式,因此也是宣扬伦理的工具。对此,樊增祥说:“本司教人,先从本原上说起,文艺何足道哉!”司法公文无一例外地充斥着“情理前置”的判断模式:在弄清事实之后,先作伦理判断,然后据此确定法律适用的原则与方法。
其次,古人认为断案的方法与作文是相同的。樊增祥认为:“看人断案犹衡文也。同题作文,而有深,有浅,有警策,有平庸,有高超卓绝,有荒谬不通。断案亦然,其不能者勿论矣。中平之吏,大致不差,其坐堂问不到深曲处,其叙详亦说不着要害处。”因此,“辩论之文,须将原批宾主分清,然后下笔。”如此才能“擿奸有术,断制有方,叙事有伦,发言有要”。总之,能够“叙事如然犀照水,断案则快剑斫断生蛟鼍”,才是一份好的法律文书。
再次,虽是“以文载道”,但是司法公文总是有固定格式的,有标准的套语。樊增祥认为,“凡讲求吏治者,率禁用四六禀词”的标准不能一刀切,“其实红禀中亦可考镜人才”,可见他并不反对禀牍的文采修饰。但樊增祥认为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应该兼顾,所谓“老手办事,具有条理,不事矜张”,才能达到“看似平淡无奇,实切实可靠”的效果。
最后,传统司法文书中书办气息陈旧。书办是府、州、县署各房书吏的通称,掌管文书,核拟稿件。大多数的司法文书是由书办起草的,书办群体的文风必然会影响到司法公文,樊增祥对于书办的“老套头,照本宣科,腐烂陈旧”之风深恶痛绝。书办在表面上,文书写作经验丰富,制作的文书也有一定章法,但是若是千文一面,只会让人望文生憎。书办的油滑之处还在于毫无态度,两面俱圆,惯用“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词语。由于书办作为州县官的辅助人员无可或缺,传统司法公文中的书办陈旧之气息似乎也无法避免。
传统司法公文的标准
明白。传统司法公文首要要求“明白”,所谓“叙述清楚,判断公平”,分为事实叙述的明白和案情分析的明白。前者针对的是事实,后者是关于法律或者情理的适用。就“事实”而言,大致上要写明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经过这样一些基本的要素,关键是叙述的前后没有矛盾。“凡作禀牍,务要眉目清楚”。含糊其辞的案情汇报,看了会让人不明所以,“焦闷万状”。就判断而言,事实叙述清晰明白后,法律文书紧接着要说理,说明适用规则的理由。这里之所以没有用“法律”而是用“规则”,原因是樊增祥对于规则的理解是“情法交尽”。他认为,“情理外无法律”,对于情理的理解往往靠的是对具体生活的体验。樊增祥经常夸奖判断准确的文书:“判断此案,入情入理,确不可易。”判词一定要合情合理,让人信服。对于民众而言,温情的情理比冰冷的律例更容易接受。
驯雅。在樊增祥眼中,民间村夫、村妇,通常言语粗俗不堪。官员审案,自然要与民人言语,就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说道理,但是给上级的案件禀详则要驯雅。他说:“对百姓说话要口才,对上司说话要文笔。”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因此,官员审案无论案情如何污秽,在法律文书中要力求雅致,“乃于秽亵之中力求驯雅。”此外,樊增祥认为,只有高水平的文雅吏才讲得清“情理法”的意识。在论证“理”在何处、“法”谓如何、“情”之表现等方面,能“推求至当”,做得出色。
简洁。司法公文的雅驯并不是把它做成骈俪文章,司法公文毕竟是对事、对理的表述,所以在明白、雅驯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的简洁。要做到简洁,就要抓住主干,剔除末节。所谓“辩论之文,须将原批宾主分清,然后下笔”。当然简洁并不是要简要,法律文书中需要说明的还是要说清楚,所以樊增祥说:“凡办案叙供,固须简洁,亦须周到。”
以上三个方面是对于司法文书的形式要求,而“实际”是对司法文书的实质要求。樊增祥言:“大凡作文惧逢里手,论事怕遇行家。所谓真人前道不得假话也。禀牍不在说得好看,须有实际。”按照樊增祥的理解,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描述真实;二是能解决纠纷。樊增祥久居县令之位,对于州县的舞文弄墨、弄虚作假的伎俩十分清楚。
对西方文体的接受与抵制
清末变法过程中翻译了大量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定法与法学著作,这些法律、著作中的西方词汇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司法公文中。西方的“改良”“权利”“平等”等词,络绎出现在司法公文之上,西方文体伴随着西方法律制度与思想的步伐,对于中国的司法公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统法制中的一些术语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如君权、三纲、株连、八议等词语,逐渐让位于自由、平等、权利、正义、法治、缓刑、时效、罪刑法定等词语。
清末宣统年间,奕励、沈家本编纂《考试法官必要》。该书借鉴了日本、德国等国司法文书的制作经验,作了与西方相一致的统一的刑事、民事判决书格式。此章程虽然没有实施,但是足以表明西方词语对于当时中国法律文书的实际影响,及当时中国对于西方司法文体的继受。在辛亥革命之前,已基本上完成了吸收、消化西方法律词语进而创立自己的法律语词体系的过程。民国法律学科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也得益于清末时期大胆输入与传播西方法律的过程。文辞与语体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伴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扩大,法律词汇、司法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在一个沉淀数千年文明的国度里,如果外来事物影响到了本国固有文化,便会刺激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并据此来抵制外来文化的侵蚀。张之洞面对西方文体的影响如是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这是当时士大夫的一种普遍看法。一方面,樊增祥对传统司法文风的僵化、腐朽予以批判;另一方面,他认为通过西方文字来革新中国司法文体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中西方的差距在于“人”而不在于“文”,所谓:“得其人则议可行,非其人则议无当,断断然矣。”在与西方文体的对比中,樊增祥往往会表现出极强的自豪感来。他说:“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独伦理词章历劫不磨,环球无两。”经济、制度的失败而引发的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于是将语言文字赋予“立国之本”的重要意义,提升到“文以载道”的高度。
然而,由于外患日深,“文字”显然与“退虏”“送穷”等当下的实际需要颇有距离。过于重文的习惯,已被认为妨碍了实业的发展。樊增祥非常珍重中国之“文”,却也明白在以“实用”为急务的现状下西方文字的侵蚀不可避免。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当时中国传统“独优”的语言文字,很快就因与学习西方的取向似有冲突而受到更多新学少年的冲击。但是,无论如何,在司法“话语权”的司法文体下,传统司法文书中的扼要雅驯、情法交织的文风在当代仍然有借鉴学习的必要。
(作者为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京ICP备13018232号-3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30016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京B2-20203552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0425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0541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京)字第181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京零字第220018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702000076号
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642 3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