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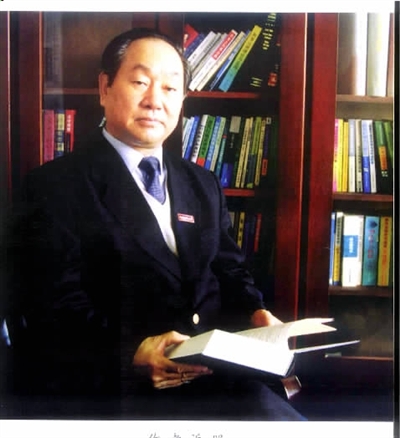
樊崇义,1940年生,河南省内乡县人。1965年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安徽省淮北的一个“五七”农场劳动。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时应召回校。1995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院名誉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诉讼法教学的开先河者
作为“文革”前法科毕业留校任教的老师,樊崇义在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被理所当然地应召返校,参加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教学工作。由于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工作刚刚起步,而北京政法学院又是当时全国法科教学的中心,在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担当重任,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樊崇义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正如他在《迈向理性刑事诉讼法学》一书的自序中所说的,“作为一个从特殊年代走过来的诉讼法学者,我亲身经历了法制虚无时代的酸楚和无奈,深知法治对国家振兴的意义,也痛感法治历程的艰辛。所以,40年来,我从未停止过对司法正义的探索,一直在为国家法制昌明摇旗呐喊。”
为了能在开学前开展正常教学活动,他以最快的速度自己动手编写讲义。由于可以借助的资料文献有限,在今天看来轻松的工作,对于他而言,却需要没日没夜地劳作、一字一句地誊改。现在难以想象在当年“无米之炊”境遇中,樊崇义写讲义的困难与艰辛。那时,樊崇义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间15平米的房子里,只有等到老人和孩子睡下后,他才能和同样是学校诉讼法学教师的夫人(韩象乾教授)坐下来写讲义。樊崇义以每日5000字的速度一干就是数月,学校总算如期开学了。那时他们也许不会想到,20年后,在樊崇义领导和主持下,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成为诉讼法学专业唯一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科研实体。自1999年揭牌成立以来,已经成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中心,发挥着国家级学术平台的作用,参与国家立法,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诉讼法学研究先进水平的重要窗口。一方面将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引进国内,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的进步。
作为教师,樊崇义一直都高度重视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其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学》从注释法学转向理性法学,使教材更加系统和富于哲理。他积极主张诉讼法学教学应当注重实践,大力推行“模拟法庭”教学法,获得多项国家级教学科研奖项。
在樊崇义的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拿到锁正杰博士论文初稿时,恰逢学校法律系组织教职工赴新马泰旅游,樊崇义不烦其重,将厚厚的博士论文打印稿带在身上,利用旅游的间歇逐页阅读,并提了百余个修改建议。论文文稿随身而行几乎成为先生的一种生活状态。多年来,樊崇义培养硕士研究生近百人,博士研究生47人,博士后3人。
诉讼法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几十年来,樊崇义笔耕不辍,著述鸿博,出版专著及合著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多部著作获教育部、北京市科研奖,较有代表性的有199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和2001年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获北京市哲社科研一等奖)。在时间跨度上,这三本书刚好涵盖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两个发展时期,是国内较有代表性的学术综述,为当时的法学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学术资源。由樊崇义担任主编的两份刊物《诉讼法学研究》和《中国诉讼法判解》,开辟了诉讼原理和案例研究等特色栏目,在推动诉讼法学的哲理化研究和诉讼实务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樊崇义还担任着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开放性文库
《诉讼法学文库》总主编一职,目前已出版了69本诉讼法学专著(还有13本正在编辑中),着力于发掘青年才俊和推介高水平诉讼法学研究成果。
学术研究应当注重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樊崇义非常重视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法制进步。2004年,他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刑事审前程序改革国际研讨会”,2006年3月组织召开了“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国际研讨会”,向海内外的学者专家们介绍了中国在审前程序改革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长期的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理论和实务研究中,樊崇义提出的许多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得到广泛认同,在诉讼法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证明标准上提倡法律真实观。证明标准问题在刑事程序和证据制度的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刑事诉讼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作回溯性证明的艰苦过程,如果采用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不仅使证明标准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会导致不择手段地追求“客观真实”,以致损害被追诉人合法权益;如果以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则有助于确立程序正义在诉讼法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所引发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论争,深化了学界对证明标准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证据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成为指导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研究和应用的基本理论。
诉讼认识论的挖掘。从哲学角度看,诉讼活动也是一种认识活动,是诉讼主体对诉讼客体(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的一种追溯性的特殊认识活动。但是,诉讼中的认识活动并不完全等同于哲学上的认识活动,而有着诸多的独特属性。樊崇义认为,应当充分认识诉讼认识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联系和区别,挖掘诉讼认识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要求,以此为基础获得对证明标准、证明对象乃至证明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的正确认识,樊崇义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我国首次提出“诉讼认识论”的科学概念。
提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影响执法效果。刑事诉讼法律观在法律文化结构的体系中,居于深层次或隐蔽的地位,但它却控制和影响着执法的效果和功能;樊崇义提出在刑事诉讼法的本质上,要从国家本位一元化的法律观转变为国家本位、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并重的多元化的法律观;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上,要逐步从国内法优位的法律观转变为国际法优位的法律观;在刑事诉讼法的价值和功能上,要从单一的和从属的工具主义的法律观转变为多种价值和功能的法律观;在运用证据的价值选择上,要从客观真实的、实质合理的法律观转变为法律真实的、形式合理的法律观,去除立法和执法中存在的“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倾向。
倡导刑事诉讼“以人为本”。樊崇义提倡把“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引入刑事诉讼领域并形成相关学术成果。在樊崇义的具体指导下,这些成果已在珠海市检察院、周口市检察院、焦作市检察院等单位加以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执法效果,社会反映也十分强烈。在转型时期,樊崇义率先提出把“伦理学”、“人学”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用“人文精神”的理念来构筑刑事诉讼程序,把“以人为本”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原理,引导学生和司法机关深入探讨学习。许多基层公检法机关在樊崇义的指导下,把人文精神运用到侦查、审判程序之中,构建了科学、文明的审讯、侦查程序。
大力推动侦查模式的转型。长期以来,刑事侦查工作深受“口供主义”影响,证据的收集和案件事实的认定,总是寄托在口供或被害人的控告上。可是,市场经济下的“人”在变,各种人证的可靠性不高。有鉴于此,樊崇义提出侦查模式要实现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变的主张。物证本位是指诉讼的进行要以实物证据的调查、收集和运用为主,以言词证据为辅的一种侦查思路和模式。当然,从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要经历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还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如比较成功的科技侦查手段。
实证研究方法的倡导者
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在教学上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主动接触社会、接触实践,才能验证理论观点,找到研究灵感。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研究之余,樊崇义积极参加各种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他是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他主张的“统一人民法院定罪原则”、“疑罪从无”,以及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完善强制措施等方面的建议对立法均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年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被国家立法部门列入立法计划,为了给立法部门和学术研究部门提供理论支持,樊崇义采取师生合作这一新的教学方式,自立项目,带领博士生撰写了《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和《正当程序文献资料选编》等完备的学术资料。
在樊崇义主持下,诉讼法学中心从2002年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侦查讯问全过程的律师在场、录音、录像”“三项制度”改革试验,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初始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几年来,樊崇义的脚印遍及近10个省(市),最后选取北京海淀、河南焦作、甘肃白银分别作为东、中和西部的代表进行三项制度试验。一个个鲜活的实例,一个个精确的数据不仅印证了侦查讯问方式改革措施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同时也为司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现实说明。2006年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开始在职务犯罪中推行讯问时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除了在大学校园里辩研法理、问道释惑,樊崇义还经常走出校门,积极为立法部门建言献策,到实践部门宣讲法理。看到自己的学术主张变为立法现实,逐渐被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接受,看到我们的国家在一步步地走向法制昌明,作为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亲身参与者,樊崇义内心的欢欣鼓舞无法言表。他豪迈地表示:“我愿把现在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再为国家法治事业奋斗二十年。”
京ICP备13018232号-3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30016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京B2-20203552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0425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0541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京)字第181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京零字第220018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702000076号
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642 3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