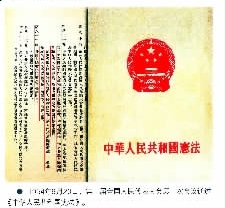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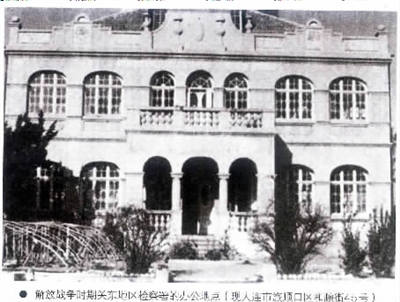
关东解放区确定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图为解放战争时期关东地区检察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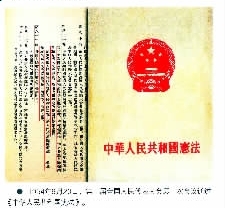
五四宪法确认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

1954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首次明确提出人民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追本溯源,中国检察制度享有监督职能可谓是源远流长。
自秦汉时始,历代王朝的御史都负有“纠察百官”、“辨明冤枉”的职责———这颇类似于今天的检察监督。1906年检察制度正式引入中国以后,“检视查验违法行为”就成了一项主要职能。
而人民检察制度一经建立,便与法律监督难舍难分。
从1932年建立苏维埃检察机构时始,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部)都被赋予一般监督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1947年6月《关东各级司法机关暂行组织条例草案》规定:“关东所有各机关、社团,无论公务人员或一般公民,对于法律是否遵守之最高检察权,均由检察官实行之。”这一规定标志着人民检察制度向法律监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定位逐渐写入党的文件和法律之中。1954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检察工作保障国家建设》。这篇社论第一次提出“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署……”
检察制度再次迎来光明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确定了检察机关的这一法律定位。
变幻的是时空,不变的是法律监督这一灵魂。
A 模仿苏联规定一般监督权
学习、移植苏联法律制度,是创建时期人民检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也是如此。
据检察理论奠基人王桂五考证,一般监督是列宁提出来的,首先实行于苏联,指的是:检察机关对有关国家机关违反法律的行政决定和措施,以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实行的检察监督活动。而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在《检察制度纲要》中,将苏联的法律监督解构为司法监督和一般监督两种。前者是检察司法机关有无违法判决与事件,后者是检察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等有无违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开始在检察工作和法学研究中使用一般监督的提法———
“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194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令”(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三条)。
在王桂五看来,这里所说的“各级政府机关”,不仅是指地方政府机关,而且包括中央政府机关。而按照法律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是无权监督中央政府机关的。因此,在1954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就改正了这种文字表述上的不确切性,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这在《王桂五论检察》一书中有深刻论述。王桂五认为,这就使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权的范围更加明确,而不至于发生误解。
对于一般监督的形式,上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提出抗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本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要求纠正;如果要求不被接受,应当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它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抗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1954年《宪法》第八十一条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给予了最高确认。
B 一般监督的典型试验
为什么要开展一般监督?李六如在《检察制度纲要》中作了说明:中国由于刚解放不久,暗害分子还很多。因此,刑事检举在检察职能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由于当时社会人员成分很复杂,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法律上的监督(指一般监督,编者注)同样不应轻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检设置了一般监督厅,厅长是老红军王立中。
但一般监督工作开展起来并不顺利。因为法律规定太宽泛,对于一般监督的认识不同,一些检察院把握不好,大到国家法令、决定,小到生活琐事都进行监督,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对此,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派人到天津、山西、河北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人啼笑皆非———一些检察院监督国营商店的螃蟹跑掉、韭菜烂掉、工厂劳动环境差、灰尘多、噪音大等小事,绝大部分案件“均够不上一般监督范围”,真正对国家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进行监督的很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53年部署的一系列试点工作、典型试验中,要求将一般监督的重点,放在监督各项财经法令的执行和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现象方面。在试点工作中,除向党政领导机关反映情况外,还应向主管机关提出纠正违法的建议。
下面这一份建议书,是难得的历史资料,由王桂五收集。当时的情况是:广东省阳春县人民检察院发现县人民委员会不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于是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建议书,要求加以纠正和改进。
阳春县人民委员会:
我院根据副检察长列席你会委员会初步所发现的问题,对你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情况依法进行了检查,经检查结果发现有下列问题:
1.阳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6月27日召开,至现在已两年又两个月,仅于1956年1月7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二次”的规定。
2.阳春县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1月10日正式成立之后,于2月18日、7月16日、9月14日先后召开三次委员会会议。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的规定。
……
根据上述情况,我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向你会提出建议书,要求你会采取措施,纠正和防止违法,以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
1.你会今后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依时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县人民委员会议。
2.你会应该组织所属干部(包括区乡干部)进行一次法律学习。因为你会的决议、措施屡次发生违法与你会干部的法律知识不高有很大关系,必须通过学习使之提高,防止违法事件继续发生。
3.你会会后作的决议、命令、措施,请抄送给我院一份。
请你会依法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此建议书,开会审查的日期应该在接信后20天内,具体时间和地点请通知我院派人员参加,并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我院。
……
兼检察长 叶超
副检察长 柯金水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阳春县人民委员会接到县检察院的建议书后,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且提出纠正不按期召开人大会议和委员会议的措施。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将阳春县检察院的建议书转发全省各县检察院,要求各县都进行一次检查。
195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接受县检察院建议,阳春县纠正了不依期召开人代会的现象》的报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了广播。不久,《南方日报》报道了广东全省各地纠正不按期召开人代会的情况。
C 一般监督“备而待用”
然而,仅仅时隔一年,类似阳春县检察院的做法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职权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一般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劳改监督等被说成是束缚专政手足,不利于对敌专政。
“监督”二字成了忌讳,法律监督变成禁区,甚至人民检察院后来也被砸烂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老检察人的个人命运也跌宕起伏,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对一般监督职能痴心不改,王桂五就是其中一位。
到了青海以后,他整日一言不发,心情非常压抑。而让他的心情“柳暗花明”甚至“兴奋起来”的,是在青海遇到了可以说明一般监督工作必要性的“鲜活个案”———
青海省委在检查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同志的错误时,发现在他主持起草的文件、报告和讲话中,有500余条是违反中央的政策、法令的。其中非常典型的是,薛克明对中央提出的“少杀长判”政策的解释。他说,少杀长判就是判刑要以十五年为起点,以二十年为标准,以无期徒刑为界限。显然,这是任意曲解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对工作的瞎指挥。
得到这个材料后,王桂五马上行动起来:“我根据批判我时涉及的问题以及我认为需澄清的问题,写了《对检察工作的若干意见》,共计十个问题,寄给了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彭真同志和高检张鼎丞检察长。在这个意见中,我反映了薛克明的500条,并据此提出了应该开展一般监督工作的意见。”
薛克明的材料果然很有说服力。很快,对王桂五的处分就撤销了。
但是,总体说来,经过多年的实践,不少人认为一般监督并不适合中国的司法实际。刘少奇、彭真曾指示检察机关可以不做一般监督工作,但要保留一般监督职权,“备而待用”。
经请示中央不搞一般监督后,法律监督的范围被总结为“一方面是进行侦查、批捕、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另一方面是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实行监督”(《1958年以来检察工作基本总结》。徐益初: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D 法律监督突出重心
“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1978年3月,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向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们解释了设置检察机关的意义。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但是,对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一直存有争议。对此,《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如何摆布?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检察机关;另一种意见希望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彭真在听取全国人大法工委汇报后,表态同意第二种意见。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提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运用列宁这一指导思想,确定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随后在本次会议上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982年通过的《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
在检察业务工作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草稿中曾保留过一般监督和民事诉讼监督条款,认为可作为刑事检察的对称———非刑事检察。但后来都被删去了。按照宪法规定,凡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开展的一般监督由权力机关承担,而司法监督权则由全国人大授权检察机关行使。所以,宪法在规定人大的职权时,尽量避免使用法律监督用语,而将这一词汇独独留给了检察机关,这与它对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是一脉相承的。
“备而待用”的一般监督正式取消后,尽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仍保留了检察机关负有“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的规定,但实践中已是鲜有运用。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范围一直在调整。除了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监督外,1982年试行、1991年通过、2007年10月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1989年4月通过的《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权。此外,1979年11月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1990年颁布的《看守所条例》第八条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1994年通过的《监狱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这些规定共同形成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完整体系。
如何认识我国法律监督的流变过程?学者甄贞等在其编著的《法律监督原论》一书中认为,虽然国家宪政文件几经修改,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也随之经历了多次调整,比如从借鉴苏联的“一般监督十司法监督”模式,到由“司法监督”缩限为“犯罪监督”,再从“犯罪监督”发展到“诉讼监督”等几种模式,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从建国初到现在一直没变,只是其外延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差异。而且这种随着社会发展态势而变化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当前,应当立足现实,抓住守法监督、执法监督和诉讼监督三个领域发展法律监督。
这番分析,对于我们梳理历史视野下的法律监督,不无裨益。
(感谢王丽丽对本文的贡献。参考资料:《王桂五论检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法律监督原论》、《人民检察史》画册)
京ICP备13018232号-3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230016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京B2-20203552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10425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第10541号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京)字第181号 |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京零字第220018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702000076号
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8642 3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