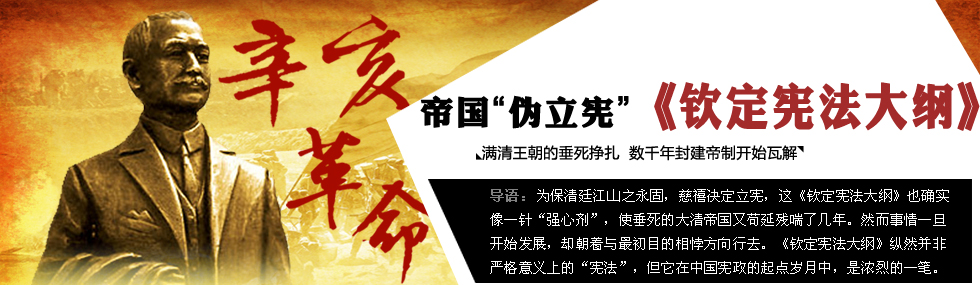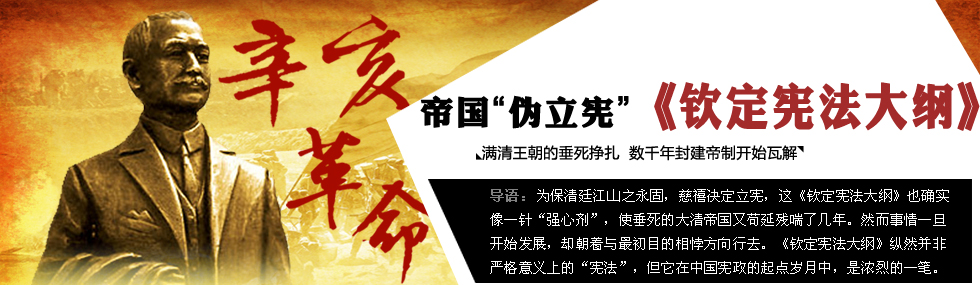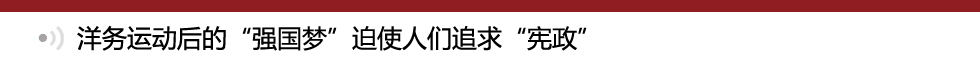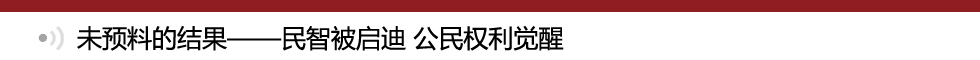《钦定宪法大纲》:伪立宪绝对主义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主要内容是"君上大权"。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而宪法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它“规制”政府权力,为公权力划定行使的界限,以防止公权力造成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损。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纲》开宗明义即规定“君上大权”并无不妥,属于立宪国家通行的做法,符合“限政”的要求。不足之处仅在于“限制”的程度无法满足后世评说者的期许而已。
关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议院法要领等,则依据权利来自君主的原则制定,"操纵之法,则必使出于上之赐予,万不可待臣民之要求","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
晚清政府是深明“规范政府权力”和“保障臣民权利”的宪政精义的,只是这场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立宪运动,在将其宪政观制度化时,做了最有利于巩固政权的处理,那就是“最弱意义上的权力限制”和“最弱意义上的权利保障”。由于是“最弱意义上”的,当然也就会引来最多的误解和最严厉的批评。